
文|筷玩思维
“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在今年315前被曝出剩菜回收等食安问题,这让许多打工人直呼“天塌了”。
作为国民级中式快餐连锁品牌以及黄焖鸡这个细分品类的绝对霸主,杨铭宇的数千家门店遍布全国,但这个品牌却屡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的信任一步步崩塌,连带着许多加盟商也被唾弃、承受着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剩菜回收”的背后不止是几个“黑心商家”的个人行为,更是餐饮从业者所共同面临的现状:低价竞争日益激烈,外加外卖平台经营成本高的双重挤压,在食材和管理上挤利润,这成了很多餐企“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当餐饮行业步入“高成本-低利润-降品质”的恶性循环,食品安全问题便成为必然的后遗症。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加盟商:总部的管理几乎形同虚设
看到新闻的瞬间,宋晓(化名)其实毫不意外,反而对于网友反应如此之大感到惊讶。在他的认知里,客单价20元以下的平价餐饮店往饭菜里添加“科技与狠活”,或者将隔夜食材再加工后继续售卖,这些都是再常规不过的操作。
宋晓曾在河北保定一家中式快餐店做过后厨勤杂工。在后厨的低温冷库里,解冻池中长期漂浮着颜色发白半透明、肉质松散的“过期”虾仁,在保水剂(焦磷酸钠)和小苏打混合液里浸泡30分钟,再放入掺着香精的双氧水中反复漂洗——砂锅里的“鲜活”食材就被端上了消费者的餐桌。
为保证出餐效率,宋晓和同事们从不清洗用来油炸的虾和小鱼,厨房纸一擦就直接抛入油锅,那些清水冲洗不掉的粘液和污渍,便借由180度的复炸油来完成“高温杀菌”。在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宋晓和同事们基本不吃店里的饭菜,有一次,厨师做了一锅新菜,他找来在后厨打杂的同事帮忙尝一下味道,被同事摆手拒绝,“你这是害我”。

私人经营的餐饮小店如此,作为全国连锁餐饮品牌的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其加盟店的卫生情况也不容乐观。早在2016年,无锡的杨铭宇加盟店就被曝使用过期肉,加工地点在偏僻的废弃工厂,卫生环境脏乱不堪,工人没有佩戴任何隔离工具,连切肉的砧板也已经发霉。除此之外,杨铭宇黄焖鸡还被曝出过“吃出老鼠”、“集体中毒”等食安事件。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拖慢了杨铭宇黄焖鸡的扩张步伐,近两年,杨铭宇黄焖鸡的门店数量大幅减少,从巅峰时期2021年的全国门店6000多家缩水至2025年的2518家。
崩塌的导火索埋在杨铭宇黄焖鸡加盟体系的裂缝中。熟悉行业的人都知道,杨铭宇黄焖鸡的品牌管理相对粗放,至今没有打磨出一个适用于规模化拓展的单店模型。
所谓的“没有适用于规模化拓展的单店模型”,在加盟商看来,就是总部的管理模式过于松散,几乎形同虚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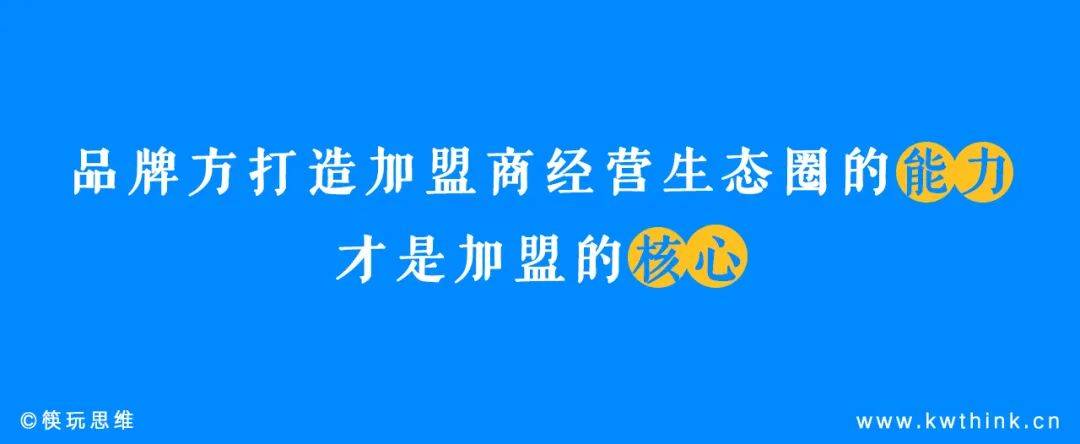
作为全国性连锁品牌,杨铭宇黄焖鸡宣称实行“全产业链管控”,但在实际运营中,所谓的管控却流于形式,多名曾经加盟或现在正在经营杨铭宇的加盟商告诉记者,在多数情况下,总部所谓的“管控”仅停留在纸面,区域代理的卫生巡查基本“靠自觉”,有时大半年才巡查一次,且会提前通知加盟商检查日期。在巡查过程中,代理们重点核查的也是采购票据,而非后厨卫生情况。
加盟商石波于2019年在江西某三线城市加盟了杨铭宇黄焖鸡,2023年合同到期后选择退出。石波认为,杨铭宇面临如今的境地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管控和审查,加盟商们开店全凭良心。
据石波回忆,总部巡查员“相比于冰柜里的冻肉有没有解冻再复冻,更关心你台账上的酱料包采购量是否达标”。
在2000多家杨铭宇加盟店里,也有严格遵守卫生管理条例的加盟商,这些门店的生意也同样受到波及。杨颖2023年9月在内蒙古开了一家杨铭宇加盟店,店里证件齐全,至今维持着较高的卫生标准,所有食材的采购记录也有账可查。每日用不完的食材,杨颖都会倒掉或喂给路过的流浪猫。
然而受风波影响,杨颖的店铺单量从每天的100余单下降至60单左右,这个时候愿意来店消费的大多是老顾客。

她感到委屈,每天在抖音直播后厨情况,为自己的店铺“鸣冤”,然而收效甚微。接连不断的食安事件消耗了公众对杨铭宇的信任,在杨颖的直播间里,不少观众不理会她的辩白,在直播间刷屏“再也不吃黄焖鸡了”。
“穷鬼套餐”横行,没有赢家成了餐饮业常态
在平价消费时代,餐饮已经成为门槛最低的创业选择,连锁餐饮品牌依靠着大量All in开店的个体加盟商、前赴后继地挺进万店行列。
作为中式米饭快餐的代表,杨铭宇黄焖鸡依靠黄焖鸡米饭这一大单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成为和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齐名的“国民快餐顶流”,吸引了大批加盟商。
2019年至今,行业经历极速变化。拌饭、煲仔饭、酸菜鱼米饭等各个品类相继崛起,消费者的正餐选择越来越多,杨铭宇黄焖鸡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其它品牌的黄焖鸡米饭,还有米饭快餐赛道的所有挑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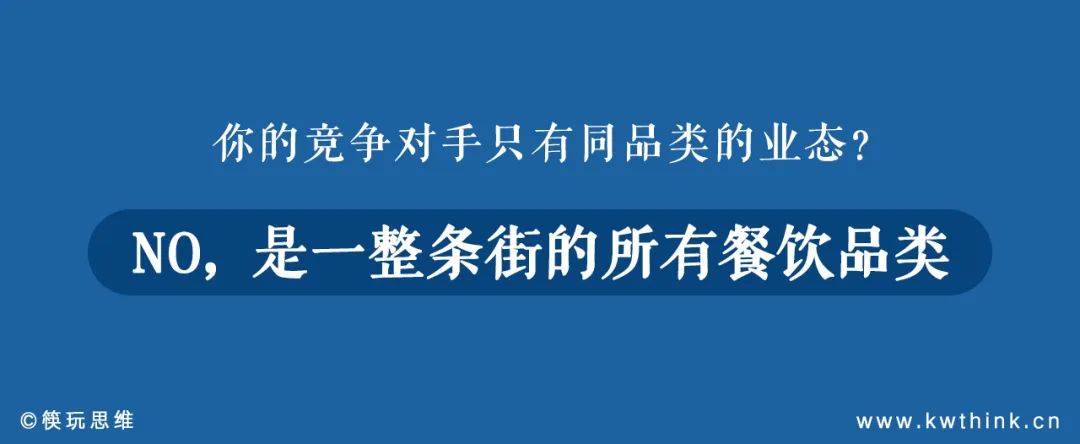
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新入场的选手试图用铺天盖地的平价“穷鬼套餐”来乱拳打死老师傅。
2024年春天,一家其它品牌的连锁中式快餐店开在了距陈安成的加盟店1公里的商圈。为给新店造势,这家快餐店推出了各类优惠活动,原价22元的盖饭仅卖18元,还额外赠送配菜和饮料。当月,不止陈安成的店铺受到影响,销量直线下滑,周围其它餐馆的订单额也都有所下滑。
本以为这只是新店开业的限时优惠,但第2个月,这家店铺继续保持着同样的优惠力度。为保住持续下滑的订单量,陈安成这名经营十余年杨铭宇门店的加盟商也不得不降价。
连锁品牌的基本打法就是“用疯狂扩张的规模来摊低供应链成本,用低价席卷市场,抢夺个体户和其它小品牌的生意,直至站稳某个细分品类”,但这个打法在奶茶和咖啡业态管用,到了中式快餐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在中国,餐饮行业的总体净利率在10%左右,而中式快餐的净利率要更低一些,目前正在冲刺上市的老乡鸡、老娘舅、乡村基等中式连锁快餐品牌,据招股书数据,近几年的平均净利率只有4%~5%。
相比奶茶、咖啡,中式快餐需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开店,房租成本居高不下,所需店员也更多,人力成本年年上涨,主打的现炒模式也拉高了原料和人工成本。
相比杨铭宇黄焖鸡,上述提及的这几家中式快餐以直营为主、加盟为辅,食品安全等有一定保障,但相对的安全也是靠推高成本换来的,在一线城市,中式快餐平均价格高达30~40元,在二线城市,一顿饭也得花费20~30元,因此,老乡鸡等品质中餐被城市白领吐槽“月薪2万也吃不起”。

更平价的中餐店意味着成本更高、利润更低,开店的老板们基本是“弯腰捡钢镚”,在价格战中仅仅维持着生存。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老餐饮人,陈安成心里清楚,房租、水电、员工工资和总部每单1.5%的运营抽成......这些都是降不下来的硬成本,降价只会导致卖出的每一单都赔钱,长期下去,结局便是关店大吉。
面对同行太过凶猛的价格战,陈安成只能选择延长开店时间。他把开店时间从过去的12小时延长至17小时——妻子白天看店,他从晚上8点待到凌晨4点。时间延长后,陈安成店铺的单量平均每天仅增长了10单左右。
这还远远不够,在没有环节可以进一步挤出利润的时候,降低食材成本似乎成了加盟商唯一的选择。
陈安成算过一笔账,正常8.5元一斤的新鲜鸡肉,店里一天至少需要80斤,如果拿3元一斤的“僵尸肉”和鲜鸡肉混着卖,成本至少可以减少30%。
“这个行业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我不降低食材成本,就要接受这几年都赚不到钱”。
压倒商家的另一座大山
在陈安成提供的2025年3月的外卖订单截图中,截至3月15日,其店铺的外卖订单有1434笔,实收33256元,扣除了活动补贴、佣金和配送服务费后,陈安成的实收为21604元,这样算下来,给到平台的费用占到营收比例约35.03%。
在平台经营的成本过高,这是外卖餐饮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外卖平台向商家提供了庞大的用户流量和配送网络,但许多餐饮商家认为,自己的辛苦经营就是在给平台打工。甚至在日单量太少的情况下,靠外卖提上来的收入连单日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了,但现在做生意又离不开外卖平台。
陈安成告诉记者,和10年前不同,人们的消费习惯早变了,如今在他的门店,外卖订单占总单量超七成。
与高订单量相伴而生的是平台的绞索越勒越紧。对商家来说,不参与优惠活动就没有流量,但做了之后,相当一部分订单收入根本进不了自己的口袋,纯粹是在给平台打工。
在外卖平台的经营成本压力之外,陈安成还需应对更为隐秘的规则博弈。去年,在参与补贴活动期间,陈安成发现外卖平台的区域代理未经授权、擅自为当地杨铭宇加盟商配置定向优惠策略。
加盟商曾多次向杨铭宇品牌方投诉这一问题,希望由总部出面解决,但未能获得有效支持。为减少损失,陈安成不得不自主监控,一旦发现品牌代理偷偷上线了满减方案,他就立即手动终止,“像防贼一样防着”。
相关部门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系统性矛盾。2022年2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引导外卖平台进一步下调餐饮商家服务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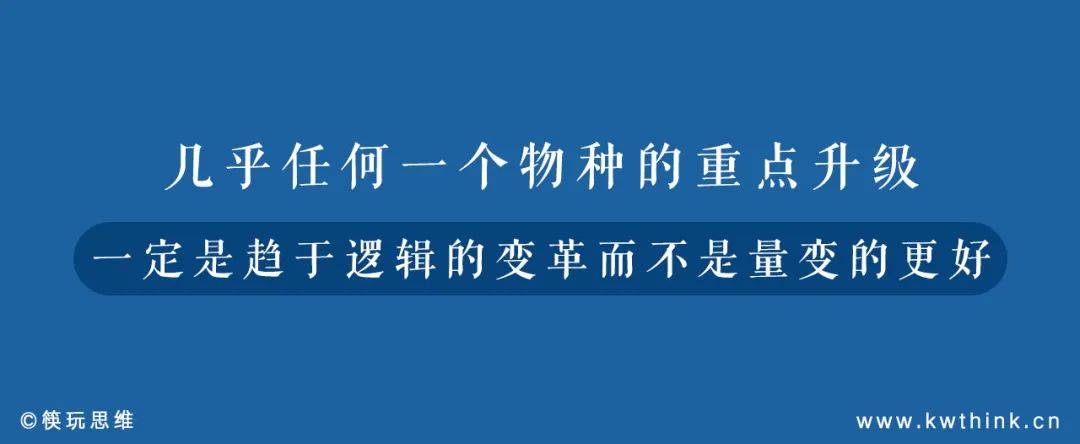
在商家的经营逻辑中,平台扣除的那部分收入并未减少。业界分析人士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平台和商家的矛盾将持续存在,这种矛盾难以在短期得到有效解决。当前,外卖平台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商家在维持高经营成本的同时,平台并未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责任。
外卖平台应该提高餐饮门店的准入门槛,同时加强有效监督,“其实加强监督的方式很简单,平台可以利用外卖骑手的力量进行监督”。平台可以设立一套激励机制,鼓励骑手一旦发现商家存在违规行为,即可通过平台提供的专门渠道进行举报,但现实情况下,这种理想化的监管提案的推行难度相当大。
据《中国餐饮品类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3月,全国餐饮门店总数接近800万家;据《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突破6000万人,日均配送订单超8000万单。超负荷的运转,使得外卖平台的监督意愿与执行空间被极大压缩。
这种无力感,正加速着陈安成们的逃离。
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选择加盟,陈安成的否定斩钉截铁。“平台要流水,总部要抽成,我们夹在中间被榨干最后一滴油”。
在激烈竞争和高额成本的双重挤压之下,陈安成逐渐接受了越来越惨淡的经营现状,已经50岁的他不想再继续卷了,只想等到孩子大学毕业,自己“完成任务就关店”。
免责声明: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内容真实性、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由用户投稿,经过编辑审核收录,不代表头部财经观点和立场。
证券投资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勿添加文章的手机号码、公众号等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
相关文章
-
宝马携超30款车型亮相上海车展 新世代驾趣概念车全球首发
2025-03-3115阅读
-
太极集团业绩崩盘,新董事长俞敏上任不足半年
2025-03-3115阅读
-
新董事长杨秀明年度业绩首秀,重庆银行“增量不增质”?
2025-03-3115阅读
-
新奥能源拟私有化,现有股东如何获利?
2025-03-3115阅读
-
联想集团2025/26财年誓师大会顺利举行
2025-03-3115阅读
-
谷歌计划将Gemini引入Chrome浏览器侧边栏
2025-03-3115阅读
-
科技巨头与航天企业因卫星频谱资源展开法律争夺战
2025-03-3115阅读
-
日料品类发展报告2025:品类持续回暖,细分赛道显现新潜力
2025-03-3115阅读
-
KTC 5K 双模果粉屏显示器 H27P3 发布,3599 元
2025-03-3115阅读
-
高通小至尊版芯片!REDMI首发骁龙8s Gen4
2025-03-3115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