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式执掌娃哈哈一年,宗馥莉一路闯过不少关隘,而眼前的这场考验,或许是她掌舵以来最严峻的一次。
一场涉及350亿元的遗产争夺战骤然爆发。2025年7月,三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宗继昌(Jacky Zong)、宗婕莉(Jessie Zong)、宗继盛(Jerry Zong)向香港高等法院及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同步发起诉讼。
三位原告主张的权益包括:追索21亿美元离岸信托资产,以及分割宗庆后生前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按当前市值计算,争议标的总额高达350亿元人民币。
350亿相当于整个“娃哈哈系”接近七年半的利润规模,这场突如其来的遗产争夺,正将娃哈哈推向一场足以撼动其多年积累的财务根基与家族控制权的风暴中心。
若争议股权归属变更,将直接动摇宗馥莉对企业的控制权。目前娃哈哈股权结构为“国有资本—职工持股平台—宗馥莉”三方制衡。若原告胜诉,股权结构将重组为“国有资本—职工持股平台—多名子女”的复杂格局,可能引发长期治理动荡。
与此同时,三位原告的母亲(网传)、娃哈哈元老杜建英的动向进一步加剧事态复杂性。据《风暴眼》报道,有娃哈哈老员工透露,杜建英已表露接手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所持娃哈哈集团46%国有股份的意向。
若此举成真,叠加股权继承诉讼结果,将直接威胁到宗馥莉作为实控人的法律基础。
宗馥莉正式掌舵娃哈哈,至今年7月已满一年。这一年中,她通过激进改革推动业绩回升,但也面临内外部多重危机,先后经历工厂停产、今麦郎代工、股权争议等多场风波。

多场风波或直接或间接指向了宗馥莉“去娃哈哈化”,向“宏胜系”战略转移的意图。而今年年初宗馥莉试图将387件“娃哈哈”商标从集团转移至宏胜系公司,被杭州国资紧急叫停,暴露其与最大股东的信任裂痕。
细究娃哈哈的股权版图,其呈现出 46% 国有股、29.4% 宗氏家族股与 24.6% 职工持股的三足鼎立格局。在宗庆后时代,凭借他个人的威望与手腕,再加上“体外娃哈哈帝国”与职工持股会的双重支撑,这一微妙的平衡才得以维系。
但对于行事雷厉风行却根基尚浅的宗馥莉来说,她尚未能驾驭这样的 “平衡术”。相同的持股比例,在她手中反而可能成为权力松动乃至坍塌的开端。
针对事件发酵,娃哈哈集团于7月13日回应称:“家族内部事务,与公司的运营及业务并无关联。公司不会提供任何答复口径或相关回应。”
娃哈哈这一表态试图将纠纷与企业经营切割,但市场不会按下暂定键。眼下正值饮料销售旺季,各大品牌价格战白热化。司法程序或许漫长,但渠道商与供应商的耐心有限。
这场遗产争夺战已不仅是法律纠纷,更是对娃哈哈商业信誉的持续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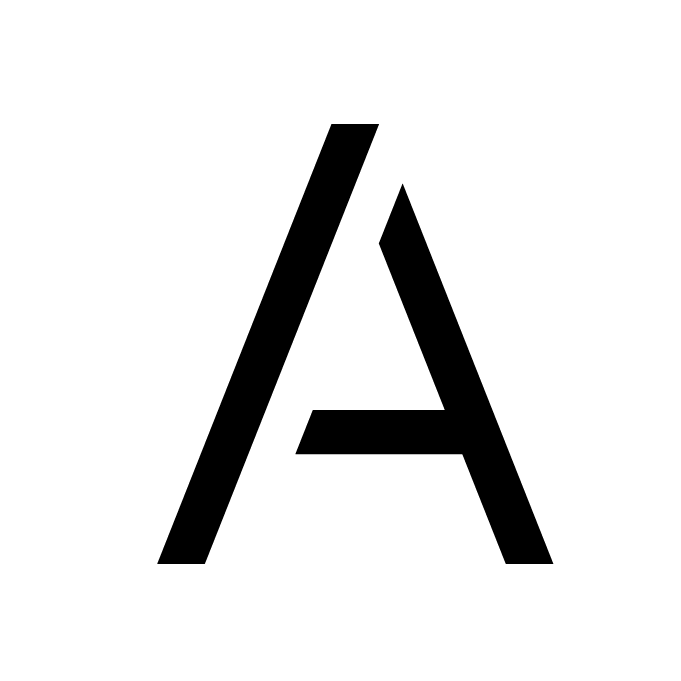
正式掌舵娃哈哈一年,宗馥莉对娃哈哈的控制权仍未稳固,这与娃哈哈复杂的股权结构不无关系。
在1999年娃哈哈集团改制后,娃哈哈已经由100%国资属性改为了混合所有制。国资持股46%,是第一大股东,宗庆后(后由宗馥莉继承)持股29.4%;职工持股会持股24.6%。
彼时,宗庆后以及家族已经成为了最大的个人股东,单从股权上看,宗庆后仍不能完全控制娃哈哈,但这丝毫不影响宗庆后对娃哈哈的绝对掌控。
原因就在于除娃哈哈本身外,宗庆后另有一个“体外娃哈哈帝国”,而这个“帝国”的存在,正是他牢牢掌控品牌、产线与渠道的关键。
“体外娃哈哈帝国”的雏形要追溯到“达娃之战”的时候。2000年左右,跨国饮料巨头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包括远在欧洲的达能集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娃哈哈与达能达成合资协议以增强企业实力。然而,合资条款中对娃哈哈的诸多限制同样影响了企业发展。
于是,娃哈哈管理层成立多家与“娃哈哈集团”无关的投资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在全国各地以“娃哈哈”加工厂的名义,投资建设了100多家娃哈哈产品加工厂,这也导致后来娃哈哈和达能之争埋下伏笔。
截至宗庆后去世前,这个“体外娃哈哈帝国”越发壮大。工商登记显示,“娃哈哈系”境内总计有200多家公司,而娃哈哈集团总计投资的只有16家,绝大部分成立于2002年之前,且皆处于非控股状态。
另一方面,从公司治理层面来看,宗庆后 “大家长式” 的集权风格与 “利益共享” 的分配理念形成互补,这使得娃哈哈职工持股会天然与他形成一致行动阵营,进而让他得以牢牢掌控娃哈哈集团的绝对话语权。
为了实现员工和企业利益一致的愿景,从2003年开始,娃哈哈就实现了全员持股。
在那场可以载入商战史册的“达娃之战”中,娃哈哈的员工表现出了极高的忠诚度。当时,达能曾通过公开声明挖角娃哈哈的管理层,从内部对其分化瓦解,然而,没有一个员工站到达能那边。
显然,宗庆后的管理有着极为浓厚的 “人治”色彩,但“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无法延续,这也直接导致宗馥莉接班之路坎坷。

宗馥莉的团队管理风格与其父大不相同,更像职业经理人,重制度、重考核,杀伐果断不留情面,这也直接导致她在搭建新的权力班底时,不断触及老臣的利益,分红改革的快速推进也令不少老员工不满。
而曾经让宗庆后江山稳固的“体外娃哈哈帝国”,对于宗馥莉而言,既是阵地,又是难啃的骨头。
体外娃哈哈帝国掌控着娃哈哈约半数以上的产能,其与集团的协同依赖宗庆后个人的指令,但根基尚浅的宗馥莉目前则缺乏这种威慑力。
除此以外,“体外娃哈哈帝国”的股东构成颇为复杂,涉及宗家亲戚、公司元老以及地方合作方等多方力量。随着权力交接的推进,各方利益诉求的差异或许会逐渐显现,无形中为企业的平稳过渡增添了变数。
这场纠纷的另一个主角杜建英,被娃哈哈内部私下称为 “影子司令”,不仅源于她曾在娃哈哈诸多重大决策背后的推动作用,更通过控股多家投资公司,实际掌控着分布于多地的子公司,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 “影子权力网”。
作为持股比例最高的一方,国资的态度在企业控制权争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凭借在娃哈哈多年积累的影响力以及手中的 “影子权力网”,杜建英也有可能成为国资扶持的对象。
届时,杜建英将手握大量股权,再加上三位非婚生子女若在股权继承诉讼中胜诉,宗馥莉原本持有的 29.4% 股权被分割后,她在公司的股权占比将大幅下降。
宗馥莉对娃哈哈的掌控根基也将彻底动摇,这无疑是她接班以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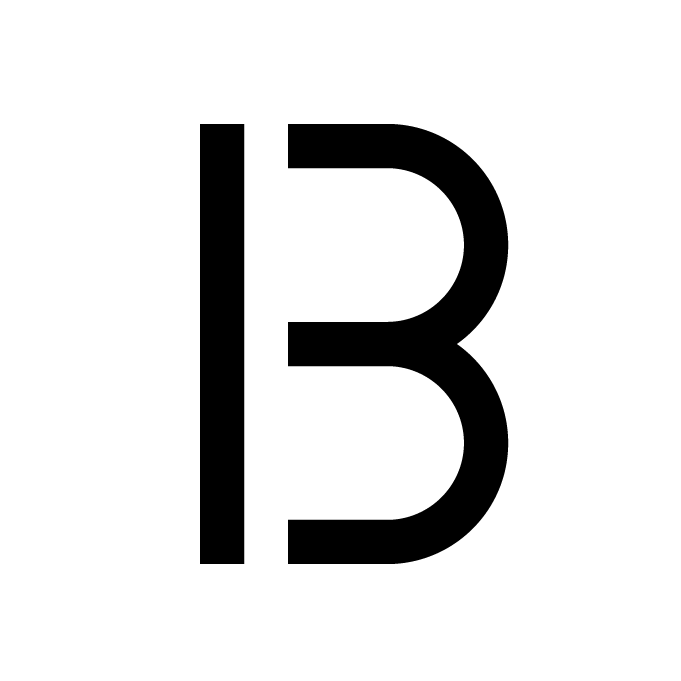
宗庆后或许未曾预料,自己精心构建的饮料帝国会因继承问题动摇根基,但却早已为宗馥莉留下了一张关键底牌 ——宏胜饮料集团。
这张底牌的威力,早在“辞任风波”中便已显现。去年7月,宗馥莉递出辞职函,称“部分股东质疑其管理合理性”,引发外界对其“权力旁落”的猜测。
7天后,宗馥莉便回归娃哈哈继续履职。回归仅一个月后,宗庆后的29.4%的股份转让给了宗馥莉,这意味着宗馥莉正式接替父亲,成为娃哈哈集团的三大股东之一。
彼时尚无股份傍身的宗馥莉之所以在这场控制权博弈中胜出,关键因素或在于这张“底牌”。
娃哈哈或许可以不需要宗馥莉,但依然需要宏胜。2007年,回国不久后的宗馥莉出任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宏胜也一跃成为娃哈哈集团的“御用代工厂”,不仅承担了娃哈哈1/3产品的加工业务,更掌握了大量娃哈哈的核心代工资源。
宏胜的重要性从此前的“代工风波”中就可窥见。给代工厂下单的公司都是“宏胜系”的公司。换句话说,这些代工厂被宗馥莉控制,无论生产环节由谁完成,利润都进入了宏胜集团。
2003年成立的宏胜集团,在股权上与娃哈哈并无关系,穿透来看由设立在海外的离岸公司恒枫贸易有限公司100%持股。而恒枫贸易由宗馥莉实际控制,这也使得宗馥莉对宏胜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
目前,宏胜集团在全国共有20个生产基地,40余家子公司,员工4000余人,拥有100多条生产线,主营产品包括果蔬饮料、瓶装饮用纯净水、矿物质水、茶饮料、含乳饮料等。

这就不难理解掌舵后,宗馥的一系列“扶植宏胜系,去娃哈哈化”的举动。
宗馥莉此前一直在宏胜饮料担任董事长一职,直到去年7月,宗馥莉职位变更为执行董事,这也意味着她有足够长的时间在宏胜培养自己的核心团队和力量。
掌舵后,宗馥莉将原娃哈哈13个核心部门逐步替换为宏胜饮料人员,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大换血,老臣退出,宏胜系高管入驻。在销售资源整合上,12省经销商合同主体也逐步变更为宏胜系公司,东北、西北市场销售资源全面转移至宏胜体系。
辞任风波一个月后,娃哈哈集团员工陆续被要求终止与娃哈哈集团的合同,改为与宏胜饮料集团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员工在娃哈哈集团历史上享有的“干股分红”待遇被彻底取消。
几乎同一时间,娃哈哈关停了深圳、大理、重庆等多地的18家工厂。与此同时,宗馥莉掌控的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在不断加大对娃哈哈产品工厂的投资建设力度。如在广东省河源投资10亿元,布局饮品及食品包装两大生产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扩大武汉宏胜恒枫饮料有限公司现有产能。
一场向“宏胜系”战略转移的大戏正在上演。
而如今这场纠纷的伏笔或早在这场“停工停产”风波的时候就埋下了。在这些停工企业中,娃哈哈集团前高管杜建英几乎均持有股权。
一系列操作下,宗馥莉不仅扩张了“宏胜系”的版图,更巩固了自己的控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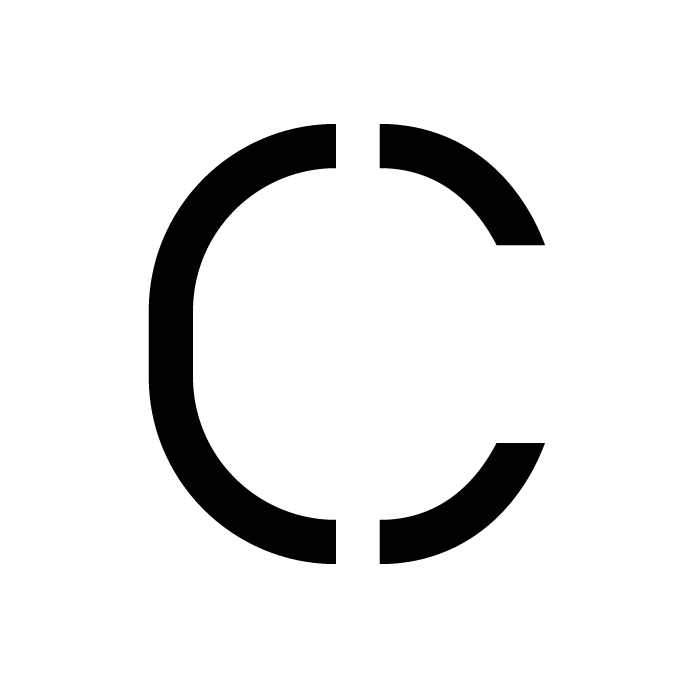
尽管宗馥莉控制着娃哈哈的部分命脉,但是由于娃哈哈的商标依然归属娃哈哈集团,集团也可以通过品牌授权来制衡宗馥莉。
虽然目前宗馥莉获得了相关的品牌授权,但倘若双方闹僵,娃哈哈在授权到期后拒绝再次对宏胜系代工厂授权,那么对于宗馥莉而言,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今年2月份,娃哈哈曾称,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升集团公司合法化经营,387件“娃哈哈”系列商标正在从母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转让给子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宗馥莉的目的,正是将商标从娃哈哈集团转移到自己的“体外娃哈哈帝国”中。一旦成功,娃哈哈集团便有可能彻底失去制衡宗馥莉的能力。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杭州国资以大股东的身份,叫停了这项交易。
交易叫停后,娃哈哈集团在 2025年5月回应称,因前期娃哈哈商标的转让目前尚处于登记备案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为此我司不排除在近期推出全新的自有品牌,并已为此次转型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2月,宗馥莉全资掌控的宏胜集团一口气注册了“娃小宗”“宗小哈”等商标,5月12日,娃哈哈家园公众号发布的一则消息中,首次出现了“娃小宗”无糖茶的身影,足见其行动之迅速。
事实上,无论是娃哈哈的股权还是商标都是改制大潮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谓历史遗留问题,源于1996年娃哈哈和法国达能的“联姻”,双方签了份《商标转让协议》,结果因为法规问题被国家商标局两度驳回,最后只能改成“租用商标”。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年,到了2007年,杭州仲裁委员会一锤定音,认为“商标归娃哈哈集团”,但达能不服,继续上诉,直到2009年才彻底和解。
宗庆后尚且徐徐图之,通过职工持股会和关联公司构建了庞大的 “体外娃哈哈帝国”,将大部分产能和利润转移至国资无法直接控制的体系外,虽未直接获得商标所有权,但通过实际运营权巩固了对品牌的掌控,既避免了与国资方的正面冲突,又通过实际运营牢牢握住了品牌的命脉。
相比之下,宗馥莉这种近乎“明抢”的方式,无疑可能触动相关方的敏感神经。

杭州国资作为持股 46%的第一大股东,应该不会坐视核心商标这一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脱离集团掌控。此次商标转让被紧急叫停,不仅暴露了宗馥莉在处理复杂利益关系上的经验不足,更可能让国资方对其产生信任危机,这也为今日可能的“大权旁落”埋下了伏笔。
而“宗小娃”等一系列新商标的注册,似乎表明宗馥莉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排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凭借手中掌控的产业链资源,再造一个“娃哈哈”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眼下这场突如其来的遗产争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控制权危机,依旧是宗馥莉掌舵娃哈哈一年来遇到的最大挑战。
宗馥莉能否在这场风波中稳住阵脚,不仅关乎她个人在娃哈哈的命运,更将决定这个国民品牌未来的走向。
免责声明: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内容真实性、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由用户投稿,经过编辑审核收录,不代表头部财经观点和立场。
证券投资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勿添加文章的手机号码、公众号等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
相关文章
-
Manus“出走”中国,为哪般?
2025-07-160阅读
-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发布超3000项前沿展品,规模刷新历届纪录
2025-07-160阅读
-
“AI女友”30美元一个月 马斯克又整活了?|科技观察
2025-07-160阅读
-
外卖大战还没结束,不知道他们图什么,但我快糖尿病了
2025-07-160阅读
-
5分钟就能“斩首”人类精子,这种藏在猫砂中的寄生虫可能已感染全球一半人口
2025-07-160阅读
-
黄仁勋:中国在AI领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希望能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更先进芯片
2025-07-160阅读
-
特斯拉官宣:“Model Y L,金秋见”
2025-07-160阅读
-
新一代作业帮学习机发布 上线“AI超级老师”重塑学习体验
2025-07-160阅读
-
全球氢硼聚变专家集结 共促未来能源革命
2025-07-160阅读
-
与黄仁勋北京对谈90分钟:54问无所不谈,夸雷军,赞华为,点名蔚小理
2025-07-160阅读

